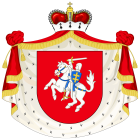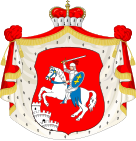鲁塞尼亚贵族(乌克兰语:Руська шляхта,白俄罗斯语:Руская шляхта,波兰语:szlachta ruska)是指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沃利尼亚的贵族,这些贵族在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和奥地利帝国,并变得越来越波兰化,后来俄罗斯化,同时保留了独立的文化身份。[1] [2] [3] [4]
鲁塞尼亚贵族,最初以东斯拉夫语和东正教为特征,[1]发现自己被不断扩大的立陶宛大公国统治,在那里它从二等地位上升到立陶宛贵族的平等伙伴。[1]在14 世纪波兰立陶宛联合之后,鲁塞尼亚贵族变得越来越波兰化,采用波兰语言和宗教(这越来越意味着从东正教信仰转变为罗马天主教)。[2] [3] [4]然而,鲁塞尼亚贵族在波兰立陶宛szlachta的身体中保留了独特的身份,导致拉丁语表达gente Ruthenus, nationale Polonus或gente Rutheni, nationale Poloni(翻译为“波兰国籍,但鲁塞尼亚血统”,[5] “鲁塞尼亚种族和波兰民族”,[6]或各种类似的脉络),尽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和维持了这种独立的身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争论,并且因时间和地点而异。[7] [8]
最终,在 1569 年卢布林联盟之后,鲁塞尼亚的大部分领土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中波兰王国的一部分。[3]鲁塞尼亚人的土地从大公国转移到波兰是在鲁塞尼亚贵族的大力支持下发生的,他们被波兰文化所吸引并渴望获得波兰贵族的特权。[3]因此,鲁塞尼亚贵族从立陶宛贵族传统转向波兰贵族,斯通将其描述为从“没有合法权利的财富”到“明确的个人和公司权利”的转变。[9]立陶宛、波兰和鲁塞尼亚贵族逐渐变得越来越统一,特别是在他们作为社会政治阶级的地位方面。[6] [10] 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鲁塞尼亚贵族变得如此严重的波兰化,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终的民族复兴主要是由中下层贵族推动的,后来又加入了日益壮大的民族新中产阶级的意识,而不是前鲁塞尼亚贵族的上层阶级。[2]
尽管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立陶宛和鲁塞尼亚发生了波兰化,但大部分下施拉赫塔人设法以各种方式保留了他们的文化身份。[11] [12] [13] [14]根据波兰人从 1930 年代开始的估计,在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地区有300,000 名普通贵族成员 - szlachta zagrodowa -居住在全国 800,000 人中。其中 90% 说乌克兰语,80% 是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徒。[15]在乌克兰其他有大量 szlachta 人口的地区,例如Bar或Ovruch 地区,尽管俄罗斯化和早期的殖民化,情况还是相似的。[16] [17]
一些主要的鲁塞尼亚贵族家族(所有这些家族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波兰化)包括Czartoryski、Sanguszko、Sapieha、Wiśniowiecki、Zasławski、Zbaraski和Ostrogski 家族。[4]
历史[编辑]
鲁塞尼亚贵族通常是东斯拉夫血统,从前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王国的公国合并的土地进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这些土地主要危害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大公国的大部分上层阶级都称自己为立陶宛人(Litvin),但讲的是鲁塞尼亚语(也称为古鲁塞尼亚语)。[18] [19]一些立陶宛贵族被Ruthenianized。[20]改编的旧教会斯拉夫语和后来的鲁塞尼亚语,在当地事务和与其他东正教公国的关系中获得了一种主要的大法官地位,作为通用语,拉丁语被用于与西欧的关系。[21]
根据白俄罗斯历史学家阿纳托尔·赫里茨基耶维奇(Anatol Hrytskievich)的说法,在16世纪,在现在的白俄罗斯境内,80%的封建领主是白俄罗斯族裔,19%是立陶宛族,1%是其他族裔。[22]他指出,立陶宛1529 年、1566 年和 1588 年的法规也保证了他们之间没有重大的种族冲突,他们的权利质量也得到了保障。[22]
波兰立陶宛联邦[编辑]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后,非波兰民族,尤其是鲁塞尼亚人和立陶宛人,受到波兰文化和语言的强烈影响。[23] [24]
波兰在该地区的影响始于 1569年卢布林联盟,当时许多以前由[20] [25] 立陶宛大公国控制的鲁塞尼亚领土被转移到波兰王室。
在波兰人或波兰化贵族对人口稀少的鲁塞尼亚土地进行殖民化的气候下,即使是来自波兰中部的农民也搬到了东方。[26] [27]
直到 16 世纪,立陶宛大公国的大多数 szlachta 都使用鲁塞尼亚语,包括大公爵和萨莫吉希亚地区,无论是在正式事务中还是在私下。[22]到 16 世纪末,在布列斯特联盟等多种情况下,随着东正教被禁止,耶稣会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 szlachta 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之一等。波兰语成为更积极地使用,特别是被巨头们使用,而次要的 szlachta 仍然 使用古鲁塞尼亚语。
从那时起,Ruthenian szlachta 积极地采用了波兰贵族的习俗和传统,例如Sarmatism。然而,尽管如此,贵族仍然在政治上忠于立陶宛大公国,并在与波兰王室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争端中捍卫其自治权。[20]
17世纪的鲁塞尼亚贵族[编辑]
哥萨克酋长国[编辑]
继乌克兰左岸佩列亚斯拉夫委员会之后,创建了哥萨克酋长国。该州的统治阶级变成了哥萨克人。尽管大量哥萨克人没有官方的(由国王和瑟姆授予或确认)贵族背景,但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 szlachta,并认为那些有官方身份的哥萨克人是平等的。这可以在生活方式、艺术、服装等方面看到。内战结束后大量鲁塞尼亚人、波兰人(例如 Zavadovsky、Dunin-Borkovsky、Modzalevsky)、立陶宛人(例如 Narbut、Zabily、Hudovych)、鞑靼人(例如 Kochubey)、塞尔维亚人(例如 Myloradovych)、希腊人(例如 Kapnist)等贵族家庭搬迁到Hetmanate。通过哥萨克人、鲁塞尼亚人和其他贵族之间的通婚,以及通过在酋长国和俄罗斯达到高位的贵族化,哥萨克人形成了哥萨克贵族,也称为哥萨克Starshyna。哥萨克贵族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他们成为俄罗斯贵族的一部分。
俄罗斯帝国[编辑]
俄罗斯帝国现代乌克兰的鲁塞尼亚贵族[编辑]
自从 16 世纪末鲁塞尼亚贵族移居俄罗斯以来,因为在波兰立陶宛联邦,他们被天主教的波兰施拉赫塔镇压,因此无法达到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和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签订后,大量鲁塞尼亚贵族和哥萨克成为酋长国的公民,该国自治但属于俄罗斯沙皇国。在哥萨克和鲁塞尼亚贵族合并为哥萨克贵族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寻求在俄罗斯获得更大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地位。从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初,他们在俄罗斯沙皇国和俄罗斯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喜欢拉祖莫夫斯基和别兹博罗德科成为帝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尽管有佩列亚斯拉夫条约,酋长国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一些哥萨克人被迫迁移到库班地区,在那里他们组建了库班哥萨克人,而大多数哥萨克人则留下了。大多数贵族血统达到等级表所需等级或被俄罗斯皇帝封为贵族的人成为俄罗斯Dvoryanstvo的一部分. 那些目前无法确认的人可以稍后再做。波兰分治后,来自乌克兰和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其他地区的鲁塞尼亚贵族也被纳入 dvoryanstvo。就像鲁塞尼亚贵族被纳入波兰贵族一样,鲁塞尼亚和哥萨克血统的高级贵族越来越多地与俄罗斯民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鲁森(Ruthenian,Cossack,Ukrainian)民族。因为大部分教育主要是用俄语和法语授课,很快鲁塞尼亚贵族开始说俄语而不是鲁辛语。通过通婚和服务,鲁塞尼亚贵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大捐助者。像彼得柴可夫斯基、尼古拉果戈理这样的人, Fedor Dostoyevsky , Ivan Paskevich , Mykhaylo Ostrohradsky是俄罗斯文化、科学和政治生活的伟大贡献者。
俄罗斯帝国现代白俄罗斯的鲁塞尼亚贵族[编辑]
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白俄罗斯的施拉赫塔人是前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上反俄起义的积极参与者。Tadeusz Kościuszko (Tadevush Kastsyushka) 是来自现在的白俄罗斯的贵族,是1793年Kościuszko 起义的领导人。Kastus Kalinouski是前立陶宛大公国领土上的 一月起义的领导人。
到了 19 世纪,一方面施拉赫塔(szlachta)的波兰化,另一方面俄罗斯东正教的俄罗斯化和暴力引入农民,导致白俄罗斯土地上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社会障碍在许多方面成为种族障碍. [28]在 19 世纪,农民出身的当地知识分子和一些 szlachta 人,如Francišak Bahuševič和Vintsent Dunin-Martsinkyevich为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做出了贡献。
20世纪初,白俄罗斯贵族主要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克拉约齐政治运动。尽管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拉曼·斯基尔蒙特或马德琳·拉齐维乌,一直同情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并支持在 1918 年建立一个独立的白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团长彼得·卡扎克维奇后来与 2000 名专业的俄罗斯哥萨克人一起参军。Pyotr Kazakevich 在加入白俄罗斯国民军之前是俄罗斯帝国的团长。
十月革命后,白俄罗斯贵族受到布尔什维克恐怖的严重打击。自 1920 年代初以来,白俄罗斯东部就已经面临苏联的恐怖,而生活在白俄罗斯西部的大多数贵族只是在 1939 年苏联吞并该领土后才受到镇压。白俄罗斯历史学家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对白俄罗斯绅士的种族灭绝。[22]
然而,到了20世纪初,白俄罗斯的许多小贵族与普通农民几乎没有区别,只有上层贵族因为出身高贵而受到压制。
奥地利帝国[编辑]
今天的鲁塞尼亚贵族[编辑]
1991年白俄罗斯恢复独立后,剩余的白俄罗斯贵族后裔成立了某些组织,特别是白俄罗斯贵族联盟(Згуртаванне беларускай шляхты)。然而,贵族之间存在分歧,他们认为自己是波兰立陶宛的 szlachta 和俄罗斯的dvoryanstvo。
命名[编辑]
最初,鲁塞尼亚贵族被称为博亚尔人(乌克兰语:бояри,罗马化: boyary ,俄语 : бояре ,罗马化:boyare ,白俄罗斯语:баяры,罗马化: bajary)。在现在的立陶宛共和国境内使用了bajorai这个词)。
在霍罗德沃特权与bajary一词一起通过后,术语bajary-szlachta (баяры-шляхта) 或简称szlachta (шляхта) 被用于主要用鲁塞尼亚语编写的立陶宛大公国的文件中。在 15 和 16 世纪,Polesia 或 Podlacha 的贵族也经常被称为ziamianie (зямяне)。自 16 世纪第二季度以来,szlachta(шляхта)这个词成为白俄罗斯语中贵族的主要术语。
宗教[编辑]
到 14 世纪,大多数白俄罗斯贵族,包括波罗的海人和鲁塞尼亚人,都信奉东正教。[需要引用] 1387 年立陶宛基督教化后,越来越多的贵族皈依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成为贵族中的主要宗教。
在 16 世纪,大部分白俄罗斯贵族,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徒,都效仿拉齐维家族,皈依了加尔文教和其他新教教堂。但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反宗教改革影响下,大部分人改信罗马天主教。由于18 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吞并了现代白俄罗斯的土地,白俄罗斯的绅士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而其余人口主要是东方天主教徒,少数东正教教徒生活在现代白俄罗斯东部。尽管如此,平斯克周围还有东正教 szlachta ,Davyd-Haradok、Slutsk和Mahiliou以及加尔文主义者szlachta。
纹章[编辑]
见波兰纹章
白俄罗斯贵族早在 14 世纪就有了他们的家族标志。Horodlo 联盟引入绅士的特权之一是使用波兰(有时修改)徽章。
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 szlachta 的徽章约有 5000 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