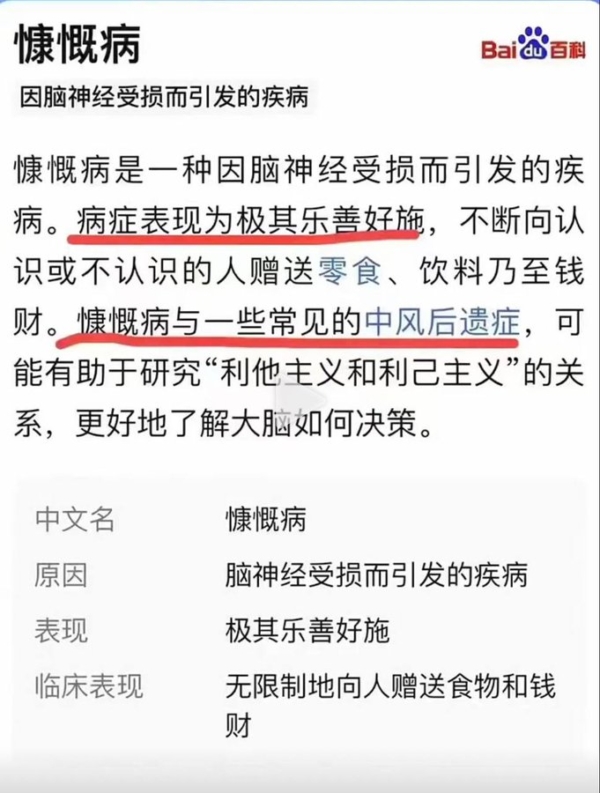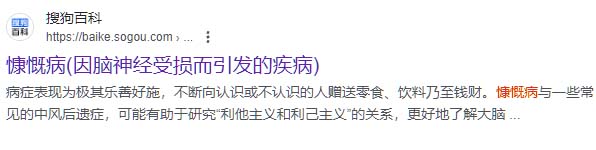今日焦点:吴国光亲身经历;文革酿中国乡下人的悲歌;随父母被劳改、下放到农村;亲眼见到被逼还俗的和尚;他呼吁知识分子,做一件事!
吴国光,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高级研究员。
他在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上世纪8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发表过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他在文中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文章得到了广泛好评,却受到中共高层的批评。
1986年,吴国光先生加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当时,组长是赵紫阳,办公室主任是鲍彤。
虽然赵紫阳所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给中国社会松绑,但在中共极权统治下,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80年代末,吴国光先生赴美治学,继续在政治评论方面深造。
【吴国光文革记忆:随家人躲避揪斗 无法上学】
谈起中共,离不开历次运动。
人们现在常说,中国大陆已经是文革再现,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的升级版。当我们问起吴国光先生关于“文革”的记忆,他说,那还得从他年幼时的一个夏日夜晚谈起。
吴国光:其实感性的印象,我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大约是1967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骑一个自行车,相当于逃亡吧,因为我母亲是教师,我父亲是干部。他们当时要被揪斗,然后我兄弟姐妹那时候被送到了我的外祖母家去,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不断受到冲击,我是家里的最大的男孩子,所以我母亲就带着我东躲西藏。
然后我父亲有一天从哪里就跑回来了,那时候都已经不可能上班工作了。他就是躲避他们抓他,抓了就是要斗,揪斗、打。那天晚上就要跑到我外祖母家去,他不敢走这个正常的路,要走一个田野里的路。那天夜里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整个田野都是鬼火,就是灵火在这个田野里飘荡。
那个地方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一个专门杀人的一个杀人场,就是有无数的生命、无数的白骨埋葬在那里,所以夏天的夜里很黑暗的时候,当然骨头里的磷就在整个空中闪耀飘荡。如果说讲起文化大革命来,这就是对我脑海中最鲜明的一个画面了。
但是,你要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说一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没有学上。文革如果以一般的说法是十年嘛,1966年到1976年,那么这之中我从不到九岁长到一个青年人,经历的东西很多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没有学上。
1966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夏天以后吧,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学上了,我那时候也不记得,因为开始文革非常地混乱了,小孩子的记忆也没有什么时间性了。那么到我在能够上学的时候,大约是我想应该是1971年的中国新年过后吧,所以大约1967、1968、1969、1970至少这四年,那么我基本上是没有学上,只有其中不到一年在一个村子里的一个村校里面读了一年书。
你刚才讲到有时文革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了,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差别很大,那尤其是说到下乡知青的话,基本上都是讲的是北京下乡知青,上海下乡知青的故事。那么我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下乡知青。所谓不典型的就是说,我其实本来就住在农村,我从小就是生活在农村,那为什么还下乡呢?是因为我是吃国库粮的,就是说我是城市户口,但是我在毛死之前一天也没有在城市生活过。
这就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拿工资的嘛,拿工资的人在农村工作,这就到农村的学校里去教书,我父母都是原来在农村的学校里,是作为拿工资的教师在那里教书。所以其实我从小住在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农村的学校,但是是周围好多农村之间的、村子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庙,那么在这个共产党来了以后,把这个庙没收了以后,就办成了一个学校,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了。
所以我这个下乡的实际上就是非常不典型的,就是说我本来就生活在农村,但是,不过是从一个从国库里面买粮食吃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变成了一个自己也成为一个到农田里去干活、挣粮食吃的这么一个人。
【打假中共虚假宣传 下乡知青 不止两千万人】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其实离我父母生活的地方不超过10公里,那这个也非常不典型。那我觉得还是你提出这个问题来,让我来谈这个事情,我还是想谈一谈。
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事情也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当时这个所谓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这个面是非常的广。那么现在的研究是说当时可能有2000万人,我个人的感觉呢,应该大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被计算在内。
就是一般来说,大家看到的下乡知青的故事,从北京到内蒙,从上海到这个黑龙江,都是大城市的。哪怕是二线城市的这个下乡知青呢,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也很少,比如说一些济南、青岛,那肯定也有,我是山东人嘛,我就讲济南青岛这样的例子,肯定也有下乡,那些中学毕业的青年当时也要下乡。
那么我的老家是山东临沂,临沂是一个地级市,当然这个临沂县城的那些年轻人也要下乡。那像我们这个连县城也不住,但是也属于城市户口的这样一些人,也要下乡。那么还有那些很多很多的人,他本来就是农村的青年,他本来就是农业的户口,但他读了书以后,也只能回到村子里来。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历史,往往就是说大家只看到浮在表面的一些这个东西,但是虽然我是这个城市户口来插到村子里去,叫插队,但是我看到那些在村子里更多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是城市户口,从来就没有离开农村的机会。他们读了书以后,回到村子里和其他的农民完全一样。
当我们回过头去讲下乡知青如何如何的时候,很少有人讲到这些完全的农村青年的命运。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我想说的,我不能完全代表这些人,但是,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类型,我就说一个不典型的下乡知青。
【文革历史真相:全中国人因此受苦】
那么我就讲毛的文化大革命给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造成的灾难,不仅仅是那些知识分子在承受,不仅仅是那些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承受,也不仅仅是城市的这样一般的民众在承受。而是中国每一个人都在承受,当时都在承受这样的苦难。那么其实越在社会底层,他们本来就苦难,那么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加倍的苦难。
当然,你像共产党的老干部们、知识分子们,他们在文革以前可能过得比较好的日子,相对说来吧,至少在物质上、生活条件上,那么文革呢,使得他们失去权利,失去原来有的特权。那么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多这样一些悲惨的记忆。文革结束以后,一旦有了机会,是他们来写历史,但是呢,更广大的受到更残酷,遭受更多苦难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来讲述他们的历史。
实际上呢,我今天愿意接受你这个采访呢,我不能代表他们讲话,但是至少我是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农村,所以,其实我也想有机会讲一下这个东西。
【吴国光:更多受苦中国人 无从讲述真实历史】
扶摇: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是不是有一些有特权的人,他们在文革之后,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而他们也有能力去把这段历史给讲述出来、给描述出来⋯⋯可是像您提到的,在农村生活的这些青年,他们本就没有这样的知识也好、能力也好,然后再加上“文革”的迫害,就更加让他们丧失了记述历史的能力,或者说,提供这些史实的能力,这是不是会让社会更加的两极化?
吴国光:其实我不是讲就是说那些知识分子也好、这个城市下乡知青也好,他们不应该写下他们的历史,就是说,就你刚才讲的,那么还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能力写下自己的历史,那我觉得作为真正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那么比如说历史学家也好、小说家也好、等等其他人也好,我觉得应该有责任去关注他们的历史,来记录他们的历史。
当然我自己不是做这个研究的,也许我们下面还会讲到,这段农村的插队的生活和我以后整个对中国社会的关心,和我对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那么还有当然我这一辈子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我在农村的时间很短了,也就是两年多一些吧,我觉得都是可能就是两年吧,对,都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我的选择。
【中国乡下人的悲歌:只有少数人能记述历史】
那么我想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有这个写历史的能力的人,更多的去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这些非常基层、非常草根的这些人的生活,把他们的历史记录下来,我想我们会对这整个社会的理解更全面、更深刻、更能抓住要害。我想这个,实际上往往就是说,当你讲这个的时候,有的人说这是不是左派的一个看法,或者等等等等。其实我想这里边是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派别的东西。
比如说毛是很关心说,你们要到农村去,好像他是让我们和农民群众结合到一起,真正的是他重视农民群众,实际上,那下面我们会讲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确实接受了,比如说我,确实接受了再教育,这个再教育是完全不是毛讲的那个意义上的再教育,也不是毛愿意看到的那种再教育。
实际上我就是讲,一个民族有这么大的人口的群体,那么如果单单写下少数人的历史,是不可能记录整个历史的。但是呢,现实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记录历史的这样一个有记录历史的能力,也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如果你去想更深的理解历史的话呢,我就想,我们要去关照那些还没有被人关照到的那些、那样一些历史的这样一个经历的人吧。
【文革下的童年:父亲被劳改 母亲被发配到农村】
扶摇:谢谢您对于底层民众的这种关心,在当今的环境下很珍贵了。我有一个疑问,您刚才提到,您在农村生活了两年,之前您提到在1968至1971年,都是没有学上,所以说,这段时间是有一部分是在县城,有一部分是在农村吗?
吴国光:我刚才讲到呢,我一直没有在县城生活过,一直到从农村毛死之后离开插队的地方,才算是进了县城。那么就是我其实一直生活在农村。但是,这个生活在农村,可以讲的就是和农民之间,叫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就是生活在这个大庙的这个院子里面,那么从我住的房子到我上学的教室之间,可能就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走路的这样一个,在我家的门口,就看到我教室的门口了。
那么下了学,我的所有的同学都是村里的孩子,但是他们都回家去了,那么我就在这校园里待下去。这个就这么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如果要是比如暑假,会到我的外祖母家,他们家也是农民,那可能会和农村的孩子在一起玩那么一点。
那这个,我想基本上就是说,虽然在形式上是生活在农村,但是,我真的是不了解,特别是到文革开始为止,就像你刚才讲,就是说我那时候还不到9岁,那么对真正的农民的生活了解的非常少。
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实际上在插队以前,我记得有两次机会是完全生活在农民之中了,那个就是生活在农民家里了。那么第一次的机会,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承受的第一个比较大的灾难,就是我父亲作为一个这个干部,他被抓去到煤矿劳改去了。然后我母亲就被从这样一个本来就是农村的学校,但是像刚才讲的,这个学校是一个和农村完全隔绝起来,就是在好几个村子中间这么一个很大的学校。
那么我们平时生活在这个校园里的,那么她就被进一步地发配到一个很偏僻的、小穷村子里的这样里面来生活,到那个村子里去教书。当然,还是拿国家发的工资,还是要到国家的粮库里去买粮食吃,但是,就她工作的地点就完全进了村子了。
那么这样,我们就到那里去住在哪里呢?在原来那个大的学校里边是住学校提供的房子,那么到了这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一所学校。这个村子的学校是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哪个地方有间房子,他们就在那地方开一个班,这样就是这么一个。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就借住在农民家里,这个农民是一个铁匠,在那里住了一年。
那时候我还年龄小,也就是十岁吧,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那一年,也许是一九六八年,这个我记不清楚。所以其实对农民也就是你每天还是和以前一样,就不过就是说你下学以后回到这个住的地方,那就看到的不再是其他的老师,而是这一家农民了。这家农民姓胡,他们家的小孩子来跟我们一起玩。那一年,对我的记忆来说还不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在村子里和那些小男孩在一起玩,这个印象还挺好。
【两位小学教师致信中央 致中国人口分布大改】
如果你现在让我回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农村生活的小学阶段,在这之前可能是一个幼儿园,我根本就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生活接下来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因为在文革的应该是一九六八年吧,这个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这在近期文革的历史当中都很少记载,但是呢,是对全中国上百万甚至可能上千万的这样一个人口,发生巨大的影响。就是山东有两个小学教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要把所有的小学都下放到村子里去办,让农民直接来管学校。
实际上农民是不会管的,实际上就是生产大队的这些党支部什么来管,实际上,他就是要把所有过去的这样一些由国家办的学校全都给它打碎,然后,让所有的这些老师都到自己的老家那个村子里去教书。
那个时候所谓老家,我妈当然愿意回她的老家,但是不可能,按照中国这样一个男权主义的观念,她必须回我爸爸的那个老家去教书。那么我大舅和我大舅妈也都是教师,那他们俩就回我妈妈那个老家那个村子去教书去了。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就回到我爷爷的那个村子去教书。
那么这个时候,我父亲还是在煤矿上劳动改造,那么我们回到我爷爷那个村子去以后,这个情况,就是我进一步深入农村生活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生活比在刚才讲的那个村子里还要差。因为刚才讲那个村子里的生活,人家毕竟知道你是一个国家派来的教师,虽然你完全在这个村子里,所以,拿你还当个客人,哪怕是文革当中对这些教师进行各种各样的迫害,但是村子里的农民是很纯朴的。他们觉得,你看你又有文化,你也是国家派来帮助我们教孩子的,对我们妈妈也好,对我们全家也好,都还是挺友好的。
那回到村子里以后,村子的人是按照村里的宗族关系来看的,你就是谁家谁家的这样一个媳妇,我妈妈不就是吴家的媳妇吗?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吴家的孙子了,回到这个村里来生活。
那么而且我爷爷住的这个村子,比我刚才讲的那个村子还要落后,他们那个学校非常差。但是我到了这里以后,我就没有学上了,因为那时候中学不再招生,我在刚才开始那个村子里上了一年的五年级,其实我没上过四年级,因为中间被耽误了。然后上了一年五年级,回来以后,那没有中学我就没事情做了。
这样,在这个村子里,其实对生活的介入就更深了,因为我们在上一个村子里头,作为国家派来的教师这样一个家庭,和村子里没有人情联系。就是说你不是说村民是你的三叔二大爷,和你有亲戚,和你有本家,你要介入他们的婚丧嫁娶,这和我们都没关系。
那么回到我爷爷这个村子,那所有这些都来了,过年你要去跟人去磕头,某一个堂姐要出嫁,你要送她出嫁等等这样一些事情。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做了两三年,那么经济生活也越来越差,那我们吃饭、各个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差。
在这个村子几年是非常非常苦的,基本上我的生活就是每天跟小朋友一起去地里挖野菜,过这样的日子。所以这一段,我把它叫做我的农村生活的初中阶段,我已经开始懂得农村乡亲之间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也懂得村里的干部可能会对村民的命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对于村里的比如说风气等等这样一些了解了吧。
但是,第一是年龄小了,那个我想十岁刚刚出头。再一个就是,我想也不光是因为年龄小理解力差吧,那么还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孩子、或者是作为一个回到本村生活的这样一个本村的出去的人后代。那么大家还是对你有一些友好,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吧,还有乡亲,那么氛围不是太差。基本上就是物质生活特别贫困,没有书读这个非常的苦恼。
还有,当然遇到生活中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吃水的问题。那么以前,在上一个村子住在这个农民家里,那个农民他们家的劳动力,会帮我们把水从很远的这个水井里打上来,挑过来,那我们靠他们帮我们供应水。当我们回到老家呢,我就是独立的一家人,不会有别人来帮我们送水的。
那么我父亲不在家,我就是我们家最大的劳动力了。那我那时候,我想那时应该是1968年,我还不到11岁,那我就自己要去井台去挑水。这个,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你要用一个很长的绳子到井底下去打水,然后挑水,而且那个村子是个小山村等等吧,这些生活的困苦都是非常严重。
所以当我下乡的时候,实际上对我来讲呢,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挑战了。就是说生活上的挑战不在于这些贫困、劳累,这些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等我下乡的时候,我是以现在回头来看的,我说那可能是我农村生活的高中阶段了,那我看到的更多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
扶摇:听您的回忆,能感受到当时相对封闭、已经开始被控制的大环境之下,农村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还是有让人难忘的温情,还是比较纯朴的,这也带给当时的您不小的慰藉。这里我想插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说,您所在的这个学校和家庭是在一个大庙里。这个大庙,它是因为当局发了一个这样的政策,然后老师下乡才把庙改成学校的呢,还是说,原本这就是本村的一个学校呢?
吴国光:这个可能在民国时代,就有可能已经征收了很多的庙产来做学校。实际上我后来,就是在北京也好、在海外也好,遇到很多朋友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我这个家庭背景有点类似,就是说是中小学教师在乡村教书的这样一些人的孩子,后来也是到大城市上了大学,后来在北京工作,到海外工作这种还有一些。说起来,好多人的学校,他们家住的学校都是当地的庙宇。
所以这个我想,因为那时候小,我没有去刻意了解,就是说我小的时候住的这个大庙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被变成学校的。但是我有一些印象,后来,其实我也有意让家里的人帮我去了解一下,到老家,到我原来住的地方去了解一下。
那么周围村子的人是讲的,这个应该是在民国时代,这个庙就被当作学校来使用了。但是,那个时代呢,民国时代当学校使用的时候呢,那个原来庙里的和尚,叫做住持,他还住在这个庙里。就是这个庙,还留了一个比如说一个房间,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了,总而言之,还有一些香火。就周围信教,也不是信教了,中国的这个都是佛教嘛,就是来拜一拜,求求平安什么之类的。所以另外的一些,更多的这个房间,就被用作小学教室了。
【中共逼和尚加入生产队 残酷打压信仰】
那么到了共产党的时代,当然就把所有的这些佛教寺庙的这些和尚都给赶出去了,因为他们当时就要毁掉所有的这样一些基层的宗教的东西吧。那么那个和尚就被赶到了我们住的这个学校大约有一里半路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口很大的水井,这个学校就到那个地方去弄水来吃。所以我们每次都跟着这个学校里的这个炊事员,到那去用一个很大的桶来装水,放在一个车子上拉回来。
那么那个井旁边就是一个院子,围着高的墙,这家人从来不和周围的人来往,他们家还养了一个很大的大狗,我们每次要和炊事员一起去,要不然小孩子很怕那个大狗。我们开始不知道,后来就说,这就是被共产党赶出来的老和尚,然后让他还俗,让他成了家,然后,他就这一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也被附近的生产队吸纳进来,成为生产队的队员,但是,因为这家老和尚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吧,也许是性格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被斗过等等吧,他总而言之就是说很少和村民来往。所以这个庙产,这个当然就是等于被政府给充公了嘛,这样就会办作公办的学校,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扶摇: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残害这些有信仰的人了。
吴国光:对,其实就是在特别是在共产党掌权的初期,就是对整个的民间的这个宗教进行这个清理、迫害、然后扼杀、然后给毁灭。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控制基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举措。
这个当然对有形的,比如像有寺庙的这样一个佛教组织,因为佛教本来也没那么组织嘛,对这个佛教徒是不会被组织到比如像教会这样的东西里面去的嘛。所以他就是靠寺庙作为一个,这个具象的这么一个中心,周围的人到这儿来,除了拜佛烧香、求子、求平安以外,一般来说,在庙旁边都有比较大的这样的地盘。
在我们那个老家那个地方会有所谓这样一个会,会就是像集一样的。我们集就是农村的rural market了,就是农村市场了,那个是供应日常的,五天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大家都能去卖点农产品,互通有无了。但是这个会呢,实际上也是一个fair,就是这么一个一年一般来说是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这是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农村集市。
那么定期一般来说是两天或者三天,那么基本上在我们老家所有的这样的会都叫庙会,为什么叫庙会呢?就是因为它都在寺庙的周围举行,因为只有寺庙,它才有这个过去有这个能力,你来的这么多人都要找水喝,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没办法想像。
不要说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哪怕是在1979年、1980年以前的中国,你出门是要自己带一个水杯,你才能有水喝的,是吧?那个时候是没有地方买水的,也没有地方去喝自来水的,这个甚至也没有地方卖水给你喝的。所以,你想在农村,这么大规模人山人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庙会,那么一般来说,那庙它能给你提供一些免费的饮水,你可以到这来喝水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庙会。
所以这个过去传统的佛教的寺庙,在农村的生活当中的扮演一个多重的角色。当然了,后来,这种有形的首先就被共产党摧毁了。那么接下来的共产党,就开始要摧毁比如说道教,因为道教就是说道观实际上不像寺庙这么普遍。
但是道教,它也是对农村的这样一个影响非常的大,因为道教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然后道教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会门了。比如说,我到在上小学的时候还能隐约记得,那个时候共产党在大肆地剿灭这个一贯道。
我记得学校里贴了各种各样的专栏,所以实际上你会看到共产党对各种各样宗教这样一个社团的清剿,从共产党开始掌权,在全国是1949年,我想在共产党的根据地那早就开始了。那么一直进行到文化大革命,那个就是到文化大革命当然就是非常彻底了。那么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当然开始有复苏,那就开始有新的这样一个清剿。
所以这个历史,其实我就是因为不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了,所以是看到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中国大陆有学者在香港出过一本书,就是讲1950年代中共如何去这个所谓改造佛教这些东西,那书就写得非常有意思。对道教特别是对一贯道,这个也有一些学者写过文章来研究,但是成体系的研究,我孤陋寡闻,应该是有的,但我还没有看到。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特别能够深入的、具体的、影响到在中国的基层社会人民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我们现在今天研究中国政治运动,大家会比如说对于批胡风、批红楼梦等等,我对这个东西关注的比较多,我对这个东西也很关注。
但是,这些东西影响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中上层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面,因为中国本来中上层知识分子这个数目就比较小,那么这个面,说起来呢,没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情的影响的面大。
扶摇:这里我也补问一下,就是说您看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共去打压这个佛教、道教的时候,它是在这个文革期间吗?
吴国光:1949年以后一直是,到文革到现在,
扶摇:后来,文革都结束了,八零年代开始有这个气功热。后来中共又镇压法轮功。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其实中共的这种文革的思维,它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结束了,可是它整个对于社会的监控,还是在文革的那种套路当中?
吴国光:当然了,这个一般呢,很多人特别是来自那些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中共的老干部,或者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喜欢把文革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变态,而不是常态,好像这个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的统治,这个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完全是对立起来的。
这个不是说没有它的道理,也有它一定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当后来习近平讲把文革和文革之前统一起来看,两个三十年接起来看,他们不满意,他们对习近平的批判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讲的这话也是有道理,因为就是说当然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
【吴国光观察:文革前后 中共本质未曾改变】
实际上,文革不过就是说,它把很多共产党的东西搞得极端化,以至于最后,特别是毛,为了他个人的这样一个极端的专权,最后把跟着他打下政权、打下江山的这些共产党的老干部们,给他出过力的知识分子们,也都反手一掌打入地狱。
只不过是这共产党内部的这样一个,出现了这样一个权力的这样一个结构的变化。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确实是,文革以前的中共和文革以后的中共,文革当中的中共,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没有制度上的大的改变。
所以呢,这也是从邓小平的年代到习近平的年代,也是同样的逻辑。只有那些在邓小平的年代,得到了特权、得到了特殊利益的人,他们才会觉得说,这习近平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反邓小平的,要把邓小平那一套捡回来。实际上,从文革前的毛泽东到文革中的毛泽东,从1990年的邓小平到今天的习近平,有很多东西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也不喜欢说只讲一样不讲区别,因为这样你对事物的认识就难以深入。这个我想就是说既要看到它们相通的、一致的,根本上是这样一贯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当然也要去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这里面的不同的改变呢?不同的改变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是觉得这两个方面都要讲。
扶摇:谢谢吴国光先生和我们分享您的亲身经历,也借此深刻分析了中共恶性体制的一脉相承。关于吴先生在文革期间的更多体会、上山下乡的见闻,以及他由此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和思考,我们留到之后的节目和您继续分享。
感谢收看《新闻大家谈》,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新闻大家谈》制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