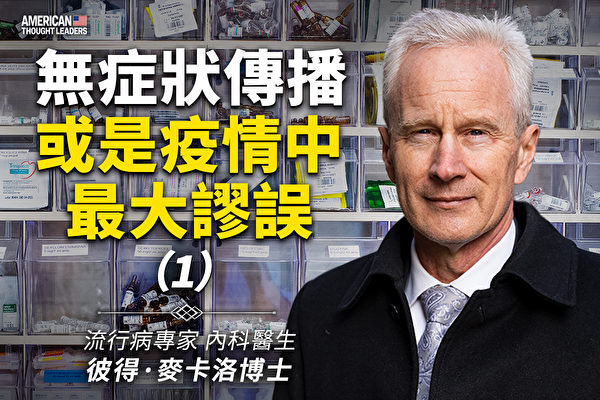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印章 | |
| 细节 | |
|---|---|
| 已确立的 | 1864 年 5 月 13 日 |
| 地点 | |
| 国家 | 美国 |
| 坐标 | 38°52′45″N 77°04′20″W坐标:38°52′45″N 77°04′20″W |
| 类型 | 国家的 |
| 拥有者 | 美国陆军部 |
| 尺寸 | 639 英亩(259 公顷) |
| 坟墓数量 | ~400,000 [1] |
| 网站 | www |
| 寻找坟墓 | 阿灵顿国家公墓 |
阿灵顿国家公墓是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美国军事公墓,与华盛顿特区隔波托马克河相望,从内战开始,639 英亩(259 公顷)的国家冲突中的死者被埋葬在这里。作为从早期战争中重新埋葬的死者。[1]美国陆军部是美国国防部(DoD)的一个组成部分,控制着墓地。
国家公墓在内战期间建立在阿灵顿宫的场地上,以前是玛莎华盛顿的曾孙女和罗伯特 E. 李的妻子玛丽安娜卡斯蒂斯李的庄园。公墓与阿灵顿故居、纪念大道、Hemicycle和阿灵顿纪念桥一起组成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历史区,于 2014 年 4 月列入国家史迹名录。 [2] [3]
历史[编辑]
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斯蒂斯,玛莎华盛顿的孙子和乔治华盛顿的养子,在 1802 年获得了现在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土地,并开始建造阿灵顿庄园,最终以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阿灵顿村命名。他的家人最初来自。遗产传给了卡斯蒂斯的女儿玛丽安娜,她嫁给了美国陆军军官罗伯特·E·李。卡斯蒂斯的遗嘱给了玛丽·李“终身遗产”,允许她在阿灵顿庄园度过余生并经营阿灵顿庄园,但不允许她出售其中的任何部分。[5]在她去世后,阿灵顿庄园传给了她的长子乔治·华盛顿·卡斯蒂斯·李。[5]该建筑以前被称为 Custis-Lee 大厦。[4]
1861 年 4 月 20 日,当美国内战在萨姆特堡开始后弗吉尼亚脱离联邦时,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辞去了他的职务,并接管了弗吉尼亚联邦的武装部队,后来成为陆军司令北弗吉尼亚州。[6] 5月7日,弗吉尼亚民兵部队占领了阿灵顿和阿灵顿宫。[7]随着同盟军占领阿灵顿的高地,联盟的首都处于一个站不住脚的军事地位。[8] 5月3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 命令欧文麦克道尔准将清除所有不忠于美国的军队的阿灵顿和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9]尽管不想离开阿灵顿宫,玛丽·李相信她的庄园很快就会被联邦士兵夺回。5 月 14 日,她在这片土地上埋葬了许多家庭珍宝,并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拉文斯沃思的姐姐的庄园。[10] [11]麦克道尔于 5 月 24 日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占领了阿灵顿。[12]
内战爆发时,大多数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战斗中阵亡的军人被安葬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士兵公墓或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亚历山大公墓,但到 1863 年底,这两个公墓几乎都已满. [13] 1862 年 7 月 16 日,国会通过立法授权美国联邦政府为国家军人死者墓地购买土地,并由美国陆军军需官负责这项计划。[13] 1864年5月,联邦军队在荒野之战中阵亡。军需官蒙哥马利 C. 梅格斯 下令对符合条件的地点进行审查,以便建立一个大型新的国家军事公墓。几周之内,他的工作人员报告说,阿灵顿庄园是该地区最合适的房产。[13]该物业很高,没有洪水(可能会挖出坟墓),可以看到哥伦比亚特区,并且在美学上令人愉悦。它也是美利坚联盟国武装部队领导人的家,战后拒绝罗伯特·E·李使用他的家是一个有价值的政治考虑。[14] 1864 年 5 月 13 日,在阿灵顿为威廉·亨利·克里斯特曼 (William Henry Christman ) 举行了第一次军事葬礼, [15]靠近现在第 27 区的东北门。[16]然而,梅格斯直到 1864 年 6 月 15 日才正式授权建立墓地。[17]直到哈里·S·杜鲁门总统于 1948 年 7 月 26 日发布第 9981 号行政命令,阿灵顿才取消其墓葬做法。[18]
政府在 1864 年以 26,800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阿灵顿,相当于今天的 464,324 美元。[19] Lee 夫人没有亲自出庭,而是派了一名代理人,试图及时支付对房产评估的 92.07 美元的财产税(相当于今天的 1,595 美元)。[20]政府拒绝了她的代理人,拒绝接受投标的付款。1874 年,他祖父遗嘱的继承人卡斯蒂斯·李( Custis Lee)将遗产委托给他的母亲,他起诉美国,声称拥有阿灵顿的所有权。1882 年 12 月 9 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李案中以 5 比 4 有利于李,裁定阿灵顿未经正当程序被没收。[20] [21]做出该决定后,国会将遗产归还给他,并于 1883 年 3 月 3 日在与战争部长罗伯特·托德·林肯 ( Robert Todd Lincoln ) 的签字仪式上以 150,000 美元(相当于 2022 年的 3,701,364 美元)将其卖回给政府。[19] [22]土地然后成为军事保留地。[23]
1929 年 5 月 30 日,赫伯特·胡佛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24]
弗里德曼村[编辑]
从 1863 年开始,联邦政府将现在被公墓占据的土地的南部用作被释放的奴隶的定居点,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弗里德曼村”。政府建造了出租房屋,最终有 1,100 到 3,000 名被解放的奴隶占据,同时耕种 1,100 英亩(450 公顷)的庄园,并在内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25]然而,在土地成为军事保留地的一部分后,政府要求村民离开。当一些人留下时,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负责人约翰·康默福德询问陆军军需官1887年,村里的人晚上从墓地取树当柴火,以关闭村子。[23] [26]军需官和战争部长随后批准了康默福德的请求。[23] 1900 年第 56 届美国国会拨款 75,000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2,442,900 美元)以解决政府对他们的债务后,该村的最后一名居民离开了。[23]
扩展[编辑]
由于空间有限,但有大量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其他退伍军人死亡并希望在阿灵顿安葬,因此在墓地增加墓地的需求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1991 年,公墓负责人小约翰·C·梅茨勒 (John C. Metzler, Jr. ) 实施了一项 140 万美元的计划,清理前 13 英亩(5.3 公顷)的停车场,为大约 9,000 个新墓地腾出空间。[27]
公墓在 1996 年[28] [29]和 2001 年[30] [31] 1999 年 [30] [31] 37 英亩(15 公顷)的土地从 NPS 控制的阿灵顿庄园获得了转让 12 英亩(4.9 公顷)林地的授权。国防部是海军附属大楼的所在地,[32] [33] 8 英亩(3.2 公顷)的土地于 1999 年从属于迈尔堡一部分的陆军部获得,[32] [34] 4 英亩( 2004 年从阿灵顿县的 Southgate 路获得 1.6 公顷的土地,[35] 2005 年从迈尔堡获得不到 10 英亩(4.0 公顷)的土地。[30] [36] [37]
2007 年,梅茨勒实施了千年计划,这是一项耗资 3500 万美元的扩建计划,开始利用阿灵顿林地、迈尔堡和海军附属土地。该项目还包括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将墓地的 40 英亩(16 公顷)未使用空间和 4 英亩(16,000 m 2)的维护财产改建为墓地,以增加 26,000 个坟墓和 5,000 个墓地。千年计划自 1960 年代以来首次扩大了墓地的物理边界,并且是自美国内战以来该地点最大的墓地扩展。[36]几个环境和历史保护组织批评了梅茨勒的计划,核动力源和阿灵顿庄园的经理也是如此。[36][37] [38]
2013 年 3 月 26 日,2013 年综合和进一步持续拨款法案(公法113-6)向国防部拨款 8400 万美元,用于规划、设计和建造千年项目。[39]该法案还拨款给国防部 1900 万美元,用于研究、规划和设计墓地墓地的未来扩展。[39]
阿灵顿森林扩张争议[编辑]
1995 年 2 月 22 日,美国内政部和美国陆军部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协议,将阿灵顿之家罗伯特·李纪念馆的一部分移交给陆军,这是阿灵顿森林的一部分。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NPS 的第 29 节,位于阿灵顿宫和迈尔堡之间。[40]财产转让涉及 12 英亩(4.9 公顷)的 NPS 土地,旨在允许 Metzler 开始将墓地扩建到其现有边界之外。[29] [41]
环保人士表示担心该协议将导致 24 英亩(9.7 公顷)的历史上重要的本土树木残余部分遭到破坏。[38] [42]林地附近的一个历史标记指出,在 1825 年访问阿灵顿故居时,拉斐特侯爵吉尔伯特杜莫蒂尔曾警告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斯蒂斯的妻子玛丽李菲茨休卡斯蒂斯:“珍惜周围的这些森林树木你的豪宅。回想一下,砍一棵树比让一棵树长起来容易得多。” 该标记进一步指出,弗吉尼亚本土植物协会已将林地视为弗吉尼亚遗留下来的古老梯田砾石林的最佳例子之一。[43]
1996 年 9 月 23 日,《1997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公法 104-201)授权内政部长将第 29 节中属于“阿灵顿国民政府”的所有土地移交给陆军部长。 Cemetery Interment Zone”和该部分的部分土地位于“Robert E. Lee Memorial Preservation Zone”内。[28] [29]
1998 年 3 月 5 日,隶属于内政部的 NPS 通知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它只想将 4 英亩(1.6 公顷)的土地转移到墓地,而不是 12 英亩(4.9 公顷) ) 1995 年的协议所描述的。作为回应,梅茨勒表示:“我很惊讶。但我们将继续与内政部合作,看看会发生什么。” [29]
1999 年 7 月 12 日,NPS 发布了一份联邦公报通知,宣布对转让进行环境评估(EA)。[41] [44] EA 表示,停泊区包含阿灵顿县最古老和最大的高潮 东部阔叶林。这片森林与曾经覆盖阿灵顿庄园的类型相同,并且是从历史上存在的树木中再生的。一项林业研究确定一棵有代表性的树有 258 年的树龄。除了保护区内的资源外,该保护区还确定包含重要的考古和文化景观资源。[44]EA 描述了四种可选的行动方案。[44]
与 NPS 1998 年 3 月向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发表的声明相比,1999 年的 EA 表示,首选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 1)将转移到墓地大约 9.6 英亩(3.9 公顷),包括大部分的停泊区和北端保护区的。[44]另一种选择(备选方案 3)将把 12 英亩(4.9 公顷)的停放区转移到墓地,同时将 12.5 英亩(5.1 公顷)的保护区保留在 NPS 管辖之下。[44] EA 得出结论:“第 104-201 号公法指示内政部长将过渡区的管辖权移交给陆军部长,这是备选方案 3 中的计划。采用任何其他备选方案都需要修改现行法律的立法行动。”[44]
2001 年 12 月 28 日,2002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公法 107-107)废除了公法 104-201 中“过时”的部分,该部分授权将第 29 条的部分内容移交给陆军部长. [31]新立法要求内政部长在 30 天内将大约 12 英亩(4.9 公顷)的停放区移交给陆军部长。[31]因此,转让涉及 1995 年协议和 1999 年 EA 中的备选方案 3 所描述的全部 12 英亩(4.9 公顷)NPS 土地。
2001 年的立法要求陆军部长将隔离区用于地下墓地和骨灰龛。[31]此外,立法要求内政部长管理第 29 条的其余部分,“永久为阿灵顿之家罗伯特·李纪念馆提供自然环境和视觉缓冲”。[31]
2012 年 12 月 12 日,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要求对一份 EA 草案发表评论,该草案将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进一步扩建描述为千禧年项目的一部分。[45] [46] [47] 2012 年的 EA 草案旨在将 17 英亩(6.9 公顷)英尺的墓地改造成墓地。Myer 场地以及 10 英亩(4.0 公顷)的第 29 节林地。EA 草案描述了七种备选方案。优选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 E)要求移除场地上 1,700 棵直径为 6 英寸(15 厘米)或更大的树木中的大约一半。大约 640 棵树位于阿灵顿森林拥有 135 年历史的部分内。[48]EA 草案得出结论:“基于对环境影响的评估......,预计拟议行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将不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将编制无重大影响的调查结果并签字。” [48]
2013 年 3 月 12 日,工程兵团发布了千年项目的修订版 EA。[49] [50]修订后的 EA 包含对 EA 草案的一些公众评论的副本,这些评论批评了该项目和 EA 的部分内容,同时提出了在公墓和其他地方附近的新军事墓地的替代地点。[51]然而,弗吉尼亚联邦林业部发现,根据 EA 草案中的信息,该项目不会对联邦的森林资源产生重大不利影响。[52]修订后的 EA 没有改变首选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 E)或陆军准备和签署 EA 草案所描述的无重大影响的发现 (FONSI) 的计划。[53]
2013 年 6 月 5 日,在审查了它收到的关于修订后的 EA 的 100 条公众意见后,工程兵团发布了最终的 EA 和已签署的千年项目 FONSI。[54] [55]最终 EA 和 FONSI 保留备选方案 E 作为首选备选方案。[54]最终的 EA 指出,在要移除的 905 棵树中,771 棵树是健康的原生树木,直径在 6 到 41 英寸之间。[56] [57]该项目将从一个不到 2.63 英亩(1.06 公顷)的区域中移除大约 211 棵树,该区域包含一个 145 年历史的森林的一部分,该森林位于历史街区的财产边界内,国家登记册历史名胜阿灵顿之家的提名表格在 1966 年进行了描述。[56] [58]大约 491 棵树将从大约 105 年树龄的树木区域中移除。[56]大约 203 棵树龄在 50 到 145 年之间的树木将从以前的野餐区移除。[56]在 2013 年 7 月 11 日的公开听证会上,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批准了千年项目的选址和建筑计划。[59]
[编辑]
1998 年,国会提议将墓地扩大到海军附属建筑和迈尔堡当时占用的土地上,这引起了人们对阿灵顿县官员没有得到适当咨询的担忧,导致该提议被撤回。[60]然而, 1999 年 10 月颁布成为法律的 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公法 106-65)随后要求国防部长移交 36 英亩(15 公顷)海军的行政管辖权陆军部长的附属财产. 该法案要求国防部长拆除附属建筑并准备将财产用作墓地的一部分,同时要求陆军部长将附属财产纳入墓地。[33]
2013 年 1 月,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县长与陆军国家军事公墓(由阿灵顿国家公墓和美国士兵和飞行员之家国家公墓组成)执行主任[61]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阿灵顿县委员会和陆军部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进一步扩大墓地。根据暂定计划,阿灵顿县将放弃地役权索斯盖特路(位于海军附件财产和公墓 2012 年边界之间),并获得沿海军附件站点西南边界的狭窄地役权,用于新的索斯盖特路。作为交换,国防部会将海军附属停车场提供给该县。
陆军还将把南乔伊斯街以西的土地转移到哥伦比亚派克到阿灵顿县。此外,弗吉尼亚联邦将把南乔伊斯街、哥伦比亚派克和南华盛顿大道界定的弗吉尼亚交通部的北半部土地大致运送到墓地。Columbia Pike 和 S. Washington Blvd 之间的立交桥。会被淘汰,发夹转在哥伦比亚派克被拉直,以提供从 S. Washington Blvd 的更安全、更自然的出口。到哥伦比亚派克。虽然没有具体说明确切的面积,并且该计划取决于弗吉尼亚联邦的合作,但如果实施谅解备忘录,将为墓地创造一个更连续的土地。[62]
然而,在 2016 年 12 月,《2017 财年国防授权法》(公法 114-328)授权陆军部长通过从阿灵顿县和弗吉尼亚联邦以谴责和其他方式收购附近的财产来扩大墓地。包含 Southgate Road、South Joyce Street 和 Washington Boulevard 通行权的墓地,包括 Washington Boulevard-Columbia Pike 立交桥。[63]陆军随后于 2017 年 6 月通知阿灵顿县政府,陆军将不再进行土地交换与县。陆军告诉该县,陆军将利用整个海军附属场地扩建墓地,并将为该墓地购置阿灵顿县当时拥有的约 5 英亩(2.0 公顷)公共土地。陆军还将获得位于哥伦比亚派克和395 号州际公路之间的大约 7 英亩(2.8 公顷)的土地用于墓地扩建,当时弗吉尼亚联邦拥有该土地。[64]
2018 年,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宣布扩建将允许增加 40,000 至 60,000 个墓葬,并将纳入现有的美国空军纪念馆。道路建设计划在 2021-2023 年进行,而实际墓地的建设计划在 2023-2025 年进行。该项目的总成本为2.74亿美元。[65]该项目占地 70 英亩(28 公顷),通过关闭和重新安置当地道路,使墓地能够利用前海军附属财产并保持连续性。哥伦比亚派克和立交桥将重新排列,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墓地空间。现有的运营综合体也将搬迁到哥伦比亚派克以南,其当前位置将成为墓地。预计扩建将使墓地保持开放到本世纪中叶。[66]
2010年管理不善争议[编辑]
2010 年 6 月 9 日,美国陆军部长 约翰 M. 麦克休在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显示墓地官员已将墓碑上的错误墓碑,浅坟中埋葬的棺材,以及相互埋葬的尸体。梅茨勒已经宣布打算在 2010 年 7 月 2 日退休,他承认犯了一些错误,但否认了有关广泛或严重管理不善的指控。[67]调查还发现,墓地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因“管理不善、缺乏既定政策和程序以及整体不健康的组织氛围”而负担沉重。[68] [69]梅茨勒和希根博坦在调查开始后不久就退休了。[70]
2011 年 3 月,由于发现的问题,最近被任命为陆军国家军事公墓的执行主任凯瑟琳康登宣布,该公墓的工作人员已从 102 人增加到 159 人。她补充说,该公墓还在购买额外的设备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设备来真正按照他们需要的标准来完成这项工作。” [71]
管理不善的争议包括限制大众媒体进入葬礼,这也被证明是有争议的。直到 2005 年,墓地的管理部门在得到家人的许可后,才允许媒体免费报道墓地的葬礼。据2008 年《华盛顿邮报》报道,从 2005 年左右开始,墓地逐渐对媒体对葬礼的报道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72]
管理层更替[编辑]
在墓地的管理争议开始结束后,陆军于 2010 年 6 月任命帕特里克·K·哈利南为墓地的代理负责人。他于 2010 年 10 月被永久提升为该职位。哈利南此前曾在国家实地项目办公室工作公墓管理局,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一个机构。Hallinan 以此身份监督了 131 个国家公墓、国家公墓政策、程序和运营。[73] 2014 年春季,凯瑟琳·康登 (Kathryn Condon) 退休后,哈利南 (Hallinan) 被提升为陆军国家军事公墓的执行主任。[74]
2014 年 5 月,Hallinan 卸任,由 Jack E. Lechner, Jr. 取代,担任墓地管理员。在加入美国陆军之前,莱克纳在私营部门担任了 10 年的葬礼主任。他晋升为上校(2011 年 11 月退休),2008 年至 2010 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供应司司长,负责监督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装备。自 2010 年 6 月起,他在 Hallinan 手下担任公墓的执行官和副主管。[74]
2015 年 8 月上旬,陆军在绩效评估“质疑他作为高级领导人成功服务的能力”后,解除了 Lechner 墓地负责人的职务。陆军拒绝进一步详细说明,并任命哈利南为临时公墓主管,直到陆军找到继任者。[75]
凯瑟琳·凯利(Katharine Kelley),前陆军军官和陆军部高级行政服务文职雇员,于 2017 年 3 月 2 日被任命为警司。[76]她于 2019 年 3 月调任另一个陆军职位。
查尔斯·R·“雷”·亚历山大,前陆军上校和陆军部高级行政服务文职雇员,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被任命为警司。[77]
美国各地的花圈[编辑]
1992 年,位于缅因州哈灵顿的 Worcester Wreath 公司在圣诞节假期结束时出现盈余。回顾童年时期的墓地之旅,公司创始人莫里尔·伍斯特(Morrill Worcester)在志愿者和当地货运公司的帮助下,向墓地捐赠了 5,000 个花圈以纪念墓地的死者,[78] 。经过 13 年的类似捐赠,2005 年,一张白雪皑皑的墓碑上覆盖着花圈的墓地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伍斯特,希望在他们自己的退伍军人墓地复制献花圈服务。[79] 2014年,志愿者第一次能够在墓地的所有部分放置花圈。[79]
150周年[编辑]
2014 年 5 月和 6 月期间,公墓通过为期一个月的一系列活动、参观和讲座来庆祝其成立 150 周年。[80]在这些庆祝活动期间,公墓官员正式将旧圆形剧场重新指定为詹姆斯·坦纳圆形剧场。詹姆斯·R·坦纳 (James R. Tanner ) 是一名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联邦陆军军官。他后来成为战争部的速记员,并记录了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调查中的大部分早期证据。他后来活跃于共和国大军,这是一个联盟军退伍军人团体。坦纳被埋在离圆形剧场几码远的地方。[81]
部分[编辑]
墓地分为70个部分,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墓地保留供将来扩建。[82]墓地东南部的第 60 节是自 2001 年以来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军人的墓地。 [83]第 21 节,也称为护士节,是为许多护士,以及西班牙裔美国战争护士纪念碑和护士纪念碑的位置。[84]另一部分——牧师山 ——包括犹太人、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军事牧师的纪念碑。
1901 年,埋葬在士兵之家和阿灵顿境内不同地点的同盟士兵被重新安葬在 1900 年国会授权的同盟部分。1914 年 6 月 4 日,同盟之女将摩西·埃西基尔设计的同盟纪念馆. 1917 年以西结去世后,他被安葬在纪念碑的底部,因为他是南方邦联军队的老兵。[85]本节中的所有同盟墓碑都是尖顶的,而不是圆形的。[86]
内战期间被称为“违禁品”的 3,800 多名以前被奴役的人被埋葬在第 27 区。他们的墓碑上标有“平民”或“公民”字样。[87]
墓碑、壁龛和墓碑[编辑]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监督国家公墓管理局的命令[88]向死者的遗产免费放置铭文和信仰标志,并提交由近亲[89]提供的信息在直立的大理石墓碑或骨灰龛位盖上。退伍军人事务部目前提供 63 个经授权的信仰标志,用于放置在标记上以代表死者的信仰。[90]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对政策的法律挑战,这一数字不断增加。[91]
2007 年之前,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 不允许在军事墓地的墓碑上使用五角星作为“信仰标志”。在帕特里克·斯图尔特 ( Patrick Stewart ) 的家人对 VA提起一系列诉讼后,这项政策在 4 月 23 日达成庭外和解后发生了变化。[92] [93] [94]
1947 年至 2001 年间,私人购买的标记被允许进入墓地。墓地允许此类标记的部分几乎已填满,墓地通常不允许在这些部分进行新的墓葬。[95]然而,墓地的较旧部分在 2001 年之前放置了各种各样的私人标记,包括大炮。[96]
有 32座英联邦战争死者墓葬,11 座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19 座来自二战[97],一些墓碑是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风格。
阿灵顿纪念圆形剧场[编辑]
无名之墓是阿灵顿纪念圆形剧场的一部分。纪念圆形剧场举办了国葬以及阵亡将士纪念日和退伍军人节仪式。复活节也举行仪式。每年约有 5,000 人参加这些节日庆典。该结构主要由佛蒙特州的帝国丹比大理石建造。圆形剧场和无名之墓之间的纪念陈列室使用意大利进口的波提奇诺石。圆形剧场是Ivory Kimball发起的一项运动的结果,该运动旨在建造一个纪念美国军人/女性的场所。国会于 1913 年 3 月 4 日批准了该结构。伍德罗·威尔逊1915 年 10 月 15 日为该建筑奠定了基石。基石包含 15 件物品,包括一本圣经和一本宪法。[98]
在阿灵顿纪念圆形剧场于 1921 年完工之前,重要的仪式在现在被称为“旧圆形剧场”的地方举行。这座建筑坐落在罗伯特·E·李曾经拥有他的花园的地方。圆形剧场于 1868 年在内战将军约翰 A. 洛根(John A. Logan) 的指导下建造。詹姆斯· A ·加菲尔德(James A.藤蔓。圆形剧场有一个大理石讲台,被称为“主席台”,上面刻着美国国家格言。美国国玺,E pluribus unum(“Out of many, one”)。主席台由时任美国陆军军需官的蒙哥马利 C. 梅格斯将军设计。[99]圆形剧场可容纳 1,500 人,并接待过William Jennings Bryan等演讲者。[100]
纪念馆[编辑]
无名烈士墓[编辑]
无名战士墓矗立在俯瞰华盛顿特区的山顶上,该墓是墓地中人迹罕至的地点之一,由科罗拉多州开采的圣诞大理石制成。它由七件组成,总重量为 79短吨(72公吨)。这座陵墓于 1932 年 4 月 9 日建成并向公众开放,耗资 48,000 美元。
其他不知名的军人后来被安置在那里的地下室,它也被称为无名之墓,尽管它从未被正式命名。埋葬在那里的士兵有: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名战士,1921 年 11 月 11 日下葬;沃伦·G·哈丁总统主持
- 二战无名战士,1958 年 5 月 30 日安葬;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
- 朝鲜战争的无名战士,同样于 1958 年 5 月 30 日被埋葬;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主持,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担任近亲
- 越南战争的无名战士,1984 年 5 月 28 日安葬;罗纳德·里根总统主持会议。1998 年 5 月 14 日,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授权下,越战无名者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并被确认为空军第一中尉迈克尔·布拉西 ( Michael J. Blassie ) 的遗体,他的家人让他们在圣彼得堡的家附近重新安葬。密苏里州路易斯。已经确定,包含越南无名氏遗骸的无名氏墓的地下室将保持空置。
自 1937 年 7 月 2 日以来,无名烈士墓一直由美国陆军守卫。1948 年 4 月 6 日,美国第3 步兵团(“老守卫”)开始守卫陵墓。守卫在看守坟墓时遵循着一丝不苟的惯例。[101]守墓人:
- 沿着坟墓后面的黑色垫子向南行进 21 步
- 向左转,面向东方持续 21 秒
- 向左转,朝北 21 秒
- 在垫子上走 21 步
- 重复该套路,直到士兵在换岗时被解除职务
每次转身后,守卫都会执行一个尖锐的“肩臂”动作,将武器放在离游客最近的肩膀上,以表示守卫站在坟墓和任何可能的威胁之间。
之所以选择二十一个,是因为它象征着可以授予的最高军事荣誉——21响礼炮。
每次转身,警卫都会做出精确的动作,然后当士兵将脚跟扣在一起时,脚跟会发出一声巨响。守卫在夏季白天每半小时更换一次,冬季白天每隔一小时更换一次,晚上每两小时更换一次(当墓地不对公众开放时),无论天气如何。
纪念邮票于 1922 年 11 月 11 日发行,纪念圆形剧场的第一个墓葬一周年。它包括原始的无名战士墓。1921 年 11 月 11 日停战日,一名身份不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士兵的遗体被埋葬,后来在 1931 年被更精致的大理石石棺覆盖。[102]
其他纪念馆[编辑]
墓地内有数座纪念碑。然而,由于墓地空间不足和纪念碑占用了大量空间,美国陆军现在需要国会联合或同时通过决议,然后才能在阿灵顿设立新的纪念碑。
无名之墓附近矗立着美国缅因号桅杆纪念碑,纪念在缅因号航空母舰上丧生的 266 名男子。纪念馆建在从船残骸中打捞出来的桅杆周围。纪念馆是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两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菲律宾的曼努埃尔·奎松和波兰 的伊格纳西·扬·帕德雷夫斯基的临时安息之地。
航天飞机 挑战者纪念馆于 1986 年 5 月 20 日投入使用,以纪念 1986 年 1 月 28 日在发射期间死亡的STS-51-L航班的机组人员。石头背面转录的是约翰·吉莱斯皮的文字Magee, Jr.诗歌High Flight,当时的总统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在谈到灾难时引用了这首诗。虽然许多遗体被确认并归还给家人进行私人埋葬,但有些遗体没有被埋葬,并被安葬在标记下。两名船员迪克·斯科比和迈克尔·史密斯被安葬在阿灵顿。2004 年 2 月 1 日,美国宇航局局长肖恩·奥基夫(Sean O'Keefe) 为2003 年 2 月 1 日哥伦比亚 号航天飞机在再入期间解体时遇难的人设立了类似的纪念碑。 [103]在哥伦比亚号灾难中丧生的宇航员劳雷尔·克拉克、大卫·布朗和迈克尔·安德森也在葬于阿灵顿。
Lockerbie Cairn 是为了纪念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 103 航班爆炸中丧生的 270 人。纪念碑由 270 块石头建造而成,每人一块在灾难中丧生。在第 64 节中,于 2002 年 9 月 11 日专门为 9月 11 日袭击五角大楼的 184 名遇难者设立了纪念碑。纪念碑呈五边形,并列出了所有遇难者的姓名。受害者身份不明的遗体被埋在它下面。[104]
1925 年 6 月 25 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批准了一项请求,要求竖立一个英联邦牺牲十字勋章,上面刻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军队中丧生的所有美国公民的名字。这座纪念碑于 1927 年 11 月 11 日投入使用,在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添加了在这些冲突中丧生的美国公民的名字。
老挝纪念碑或美国老兵纪念碑,致力于在越南战争期间与美国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顾问一起服役的老挝和苗族退伍军人,以保卫老挝王国免受北越入侵老挝,位于格兰特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永恒火焰纪念碑附近的大道。[105]
2012 年,国会开始通过立法批准在墓地设立“纪念场所”。纪念馆将是一个骨库,旨在容纳通过 DNA 分析无法识别的遗骸碎片。遗体将在放置在纪念馆之前火化。[106]
埋葬程序[编辑]
墓地里的旗帜每天从第一次葬礼前半小时到最后一次葬礼后半小时降半旗。葬礼通常每周举行五天,周末除外。[107] [108]
葬礼,包括安葬和安葬,平均每天 27 到 30 次。墓地每年进行大约 6,900 次葬礼。[87]
该公墓拥有超过 400,000 个葬礼,[1]是美国所有国家公墓中墓葬数量第二多的。130 个国家公墓中最大的一个是位于纽约州里弗黑德附近的长岛的卡尔弗顿国家公墓,每年举行 7,000 多场葬礼。
除了地下埋葬外,该墓地还拥有该国较大的骨灰安置所之一。目前正在使用四个法院,每个法院有 5,000 个壁龛。建成后,将有九个院落,共计50,000个龛位;可容纳 100,000 个遗骸。任何光荣退伍的退伍军人如果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训练除外)担任现役,则有资格在骨灰安置所安葬。[109]
埋葬标准[编辑]
美国联邦法规 (CFR) 第 32篇第 553 部分(陆军国家军事公墓)规定了公墓的规定,包括安葬(地埋)和安葬的资格。[110]由于空间有限,地面埋葬资格的标准比其他国家墓地更严格,也比骨灰安置所更严格。
除非另有禁止,以下指定的人有资格在墓地进行地葬。[111]前武装部队成员的最后一个现役时期必须光荣地结束。安葬可能是棺材或火化的遗体。
- 武装部队的任何现役成员(仅现役训练的成员除外)
- 任何退休并有资格从军队服役中获得退休金的退伍军人,包括从预备役部队退役并服役一段时间(训练除外)的现役军人
- 任何前武装部队成员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前因医疗原因光荣离职,并且在出院当天被评定为 30% 或更高的残疾
- 任何曾被授予下列勋章之一的前武装部队成员:
- 任何现役(训练除外)并担任以下任何职务的前武装部队成员:
- 美国政府的选举办公室(例如在国会任职)
- 美国首席大法官办公室或美国最高法院副大法官办公室
- 在此人担任该职位时,在 5 USC 5312 或 5313(行政附表的 I 级和 II 级)中列出的办公室
- 根据 1946 年 8 月 13 日法案第 411 条第 60 条的规定,在其任期内的任何时间被归类为 I 类的使团负责人。1002,经修订 (22 USC 866) 或在 1988 年 3 月 21 日的国务院备忘录中列出
- 任何前战俘,作为战俘,在现役军人、海军或空军服役中光荣服役,其最后一个军事、海军或空军服役期光荣终止,并于 1993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后死亡
- 上述任何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的配偶、寡妇或鳏夫、未成年子女或永久受抚养子女以及某些未婚成年子女
- 寡妇或鳏夫:
- 在海上失踪或被埋葬或从飞机上掉下来或正式确定永久失踪的武装部队成员,其状态为失踪或行动中失踪
- 一名武装部队成员,被安葬在由美国战争纪念碑委员会维护的海外美军墓地
- 已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任何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永久受抚养子女
- 根据父母的资格,未成年子女或永久受抚养子女的父母已被安葬在阿灵顿。与主要资格离婚或丧偶再婚的配偶不符合安葬资格
- 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前武装部队成员可以与已被埋葬且是主要资格的近亲一起埋葬在同一个坟墓中
骨灰安置所的标准[编辑]
至少部分由于墓地缺乏地面埋葬空间,骨灰安置所的安葬标准(火化遗体的埋葬)目前的限制性远低于墓地的地面埋葬。一般而言,任何现役(训练除外)且最后一次服役光荣终止的前武装部队成员都有资格获得入职资格。32 CFR § 553.15a全面描述了入职资格。
禁止安葬或纪念[编辑]
国会不时制定禁止类别的人,即使有资格埋葬,也会失去该资格。一项此类禁令是针对某些因犯有某些州或联邦死刑罪而被定罪的人,如38 US Code § 2411中所定义。死刑是法规中明确定义的术语,对于国家罪行,可以包括有资格判处无期徒刑的罪行(有或没有假释)。这项规定最初的原因是为了阻止蒂莫西·麦克维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获得资格,但后来对其进行了修改以阻止其他人。[112]
同一法规还禁止那些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确定通过死亡或逃跑来避免这种定罪的人。[需要引用]
著名的墓葬[编辑]
第一个被埋葬在阿灵顿的士兵是1864 年 5 月 13 日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亨利克里斯特曼。 [113]阿灵顿国家公墓埋葬了396名荣誉勋章获得者。[114]
在阿灵顿举行了五场国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和约翰·肯尼迪总统、他的两个兄弟参议员 罗伯特·肯尼迪和参议员爱德华·“泰德”·肯尼迪,以及陆军上将 约翰·J·潘兴的葬礼。无论他们是否是战时服役人员,美国总统都有资格被安葬在阿灵顿,因为他们作为总司令监督武装部队。[115]
墓地中最常参观的地方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和杰奎琳·肯尼迪的坟墓,他们与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和死产的女儿阿拉贝拉一起被埋葬在附近。肯尼迪的遗体于 1967 年 3 月 14 日被安葬在那里,这是从他原来的阿灵顿墓地重新安葬的地方,大约 20 英尺(6.1 m)外,他于 1963 年 11 月被安葬在那里。坟墓标有“永恒的火焰”。他的兄弟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和参议员爱德华·M·“泰德” ·肯尼迪的遗体被埋葬在附近。后两个坟墓标有简单的十字架和脚石。1971年12月1日,罗伯特肯尼迪的尸体被重新埋葬距其 1968 年 6 月的原始墓地 100 英尺(30 m)。
1967 年 1 月 27 日,两名宇航员在阿波罗 1 号指挥舱内的闪火中丧生, Gus Grissom和Roger Chaffee被埋葬在墓地。约翰·格伦是第一位绕地球运行的美国人,也是俄亥俄州的一位长期美国参议员,他于 2017 年 4 月被埋葬在墓地。[116]
英国 外交官和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在二战期间在华盛顿特区去世时被埋葬在墓地。[117]迪尔坟墓上的骑马雕像是墓地仅有的两座此类雕像之一。另一个是菲利普·卡尼少将的。[118]
劳里·托尔尼 ( Lauri Törni ) 因在冬季战争期间曾在芬兰军队服役、在二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在越南战争期间曾在美国军队服役而闻名,他被安葬在阿灵顿。他是唯一一位被安葬在这里的前武装党卫军成员。[119]
访客要求[编辑]
2016 年,墓地宣布了限制游客进入墓地的政策和程序,其中一些被认为可能会给游客造成延误。
自行车使用[编辑]
根据 2016 年制定的陆军部最终规则,[120]墓地的自行车政策规定骑自行车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并且只能在持有家庭通行证的情况下进入。[121]
安全程序[编辑]
2016 年 9 月,墓地的代理主管 Hallinan 宣布墓地正在加强对其游客的安全措施。除了已经实施的随机身份检查和其他安全措施外,墓地还要求行人在设定的入口点进入:纪念大道的主入口、Ord 和 Weitzel 大门,以及 Joint Base Myer- 的 Old Post Chapel 大门。亨德森大厅。在通过其正门进入墓地之前,所有行人现在都通过墓地的欢迎中心进行筛选。进入墓地时,所有车辆通行都需要出示由政府签发的带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例如驾照或护照。车辆也接受随机检查。Hallinan 表示,这些过程可能会导致进入墓地时出现延误。[122]
另见[编辑]
注释[编辑]
- ^ a b c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www.arlingtoncemetery.mil。于2020 年 12 月 24 日从原版存档。2020年12 月 20 日检索。